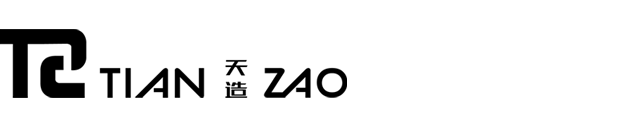文/加肥猫
编辑/Spiral@顶尖文案Topys

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
这是沈从文先生的名句。少年时代,一下子读到它,不觉悠然神往。那时候,我只行过自家的门槛,只看过自家窗口的云,还偷偷地喝过一点啤酒,年龄太小,领略不到妙处,感觉与猫尿的气味颇为类似。但我有个神秘的预感,自己即将遇到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了!最大的问题是,我居然还没准备好!有朝一日面对她时,我没资格对她讲出这句优美的台词!为了取得讲这句台词的资格,我才背上了沉重的行囊!
我知道,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生性好动的人,他们并非像我一样踏上征程。他们自称是“驴”。他们如同一名忠诚的职业杀手,手里攥了一份名单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杀手的使命是把名单所列的人物全部干掉,“驴”的使命是把名单上所列的地名全部走完。“驴”的名单通常是某些排行榜,譬如“世界上你必须要去的XX个地方”,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去,就觉得抱憾此生。至于杀掉这些人,走完这些地方,究竟有何深意,杀手的特点是从来不问为什么,“驴”也不喜欢安静下来思索,他们习惯抬蹄就走。
有些头脑聪明一点的“驴”,喜欢在网络上发布攻略,热心地提供诸如此类的信息:坐过的车次、看过的美景、住过的旅馆、吃过的小菜……从地点到价格,巨细靡遗。他们乐于看到别人跟随自己的方向,拷贝自己的体验,重复自己的感受。他们帮助了后来者,也剥夺了后来者冒险的乐趣。总之,资讯的过于发达,使得“驴”每次抵达一个新的去处时,头脑中早已装满了二手经验,新鲜不再。
就本性而言,我是一个惫懒的人。去了一些众口相传的名胜之地,却也无甚惊喜,回想起来,只是一团团模糊的印象。最大的乐趣还是,我取得了说那句台词的资格。后来,遇到了一个机会,很痛快地把这句台词说了。说完后,我有些后悔,自己操之过急了,她似乎不是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;然而,我缺乏耐心,按捺不住,又找了一个机会说了一次,还是隐隐地觉得不对。就这样,一再肯定,一再否定,直到现在,我觉得还是没有遇到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
与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·佩索阿委实相见恨晚。如果能早些读到他的这本《惶然录》,就不必如此折腾了。他是我所见最讨厌旅行的人。佩索阿直截了当地说:“如果我想象什么,我就能看见它。如果我旅行的话,我会看得到更多的什么吗?只有想象的极端贫弱,才能为意在感受的旅行提供辩解。”
他振振有词地说:“我对世界七大洲的任何地方既没有兴趣,也没有真正去看过。我游历我自己的第八大洲。有些人航游了每一个大洋,但很少航游他自己的单调。我的航程比所有人的都要遥远。我见过的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。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市。我渡过的大河在一个不可能的世界里奔流不息,在我沉思的凝视下确凿无疑地奔流。如果旅行的话,我只能找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复制品,它复制着我无须旅行就已经看见了的东西。”
托佩索阿的福,我不必再为自己没有去过什么地方惶恐不安了,拥有宏大丰富的内心才是更加要紧的事。它是名单和排行榜上找不到的第八大洲,或许壮美,或许贫乏,但它是唯我专属的世界。
至于那句优美的台词,只要略作改动,就完全符合我的现状了。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也爱过一打儿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这样也不算太坏啊。

关于佩索阿
费尔南多·佩索阿(Fernando Pessoa,1888年6月13日-1935年11月30日)生于里斯本,是葡萄牙诗人与作家。 他生前以诗集《使命》而闻名于世。 他被认为是继卡蒙斯之后最伟大的葡语作家。文评家卜伦在他的作品《西方正典》形容为他是与诺贝尔奖得主巴勃鲁·聂鲁达最能够代表二十世纪的诗人。
《惶然录》书摘
“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彻底的平静,与此相反,倒是一再受扰于有关什么是平静的解说,还有我们对平静的渴求。”(《也许有心灵的科学》)
“我的自闭不是对快乐的寻求,我无心去赢得快乐。我的自闭也不是对平静的寻求,平静的获得仅仅取决于它从来就不会失去。我寻找的是沉睡,是熄灭,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放弃。”(《时光的微笑》)
“你想要旅行吗?要旅行的话,你只需要存在就行。在我身体的列车里,在我的命运旅行途中如同一站接一站的一日复一日里,我探出头去看见了街道和广场,看见了姿势和面容,它们总是相同,一如它们总是相异。说到底,命运是穿越所有景观的通道。
如果我想什么,我就能看见它。如果我旅行的话,我会看得到更多的什么吗?只有想象的极端贫弱,才能为意在感受的旅行提供辩解。
‘通向N市的任何一条道路,都会把你引向世界的终点。’但是,一旦你把世界完全看了个透,世界的终点就与你出发时的N市没有什么两样。事实上,世界的终点以及世界的起点,只不过是我们有关世界的概念。仅仅是在我们的内心里,景观才成其为景观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想像它们,我就是在创造它们。如果我创造它们,它们就存在。如果它们存在,那么我看见它们就像我看见别的景观。所以干嘛要旅行呢?在马德里,在柏林,在波斯,在中国,在南极和北极,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有异于内在的我?可以感受到我特别不同的感受?
生活全看我们是如何把它造就。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。我们看到的,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,而是我们自己。\"(《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》)
“我觉得我爱这一切,也许这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爱,或者,即使世上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任何心灵所爱,而多愁善感的我却必须爱有所及。我可以滥情于区区一个墨水瓶之微,就像滥情于行空中巨大无边的冷漠。”(《被上帝剥削》)
“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。我们所有人对自由怯懦的爱,是无可辩驳的证据,证明我们的奴隶生活是如何与我们般配——因为一旦自由降临我们,我们全会将其当作一件太新鲜、太奇怪的东西而避之不及。”(《个性与灵魂》)
佩索阿诗选(韦白译)
■虚无
哎,那轻柔的、轻柔的演奏,
像某人想要哭,
一首歌,从技巧
和月光里摇荡着飘出……
虚无让我们回想起
生活。
谦恭的前奏
或者一个淡出的微笑……
一个远处的寒冷的花园……
而在发现它的灵魂里,
只是它荒谬的回音空洞地
飞行。
1922年11月8日
■你不喜欢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
你不喜欢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:
你仅仅度过了它。无论你过着什么样的
没有喜悦的生活,你都没有生活。
你无须去爱,或者去饮酒或者微笑。
阳光倒映在水坑里
就足够了,如果它令你愉悦。
幸福的人,把他们的欢乐
放在微小的事物里,永远也不会剥夺
属于每一天的、天然的财富。
1933年3月14
■轻轻地诉说,因为这是生活
轻轻地诉说,因为这是生活,
这是生活和我对生活的意识,
因为夜晚继续前行,我累了,我睡不着,
而如果我走到窗前
我看到,在那野兽的眼皮下,
有无数星星的巢穴……
我消磨了白昼,希望能在夜晚安睡。
此刻正是夜晚,差不多是下一天了。
我昏昏欲睡。我睡不着。
我感到,在这种疲倦中,我是整个的人类。
正是这种疲倦,几乎把我的骨头融化成了肉……
我们全都分享着这同样的命运……
带着被缚的翅膀飞行,我们蹒跚着
穿过世界,一张横贯深渊的蜘蛛网。